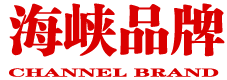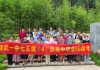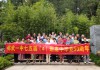谁对谁错
危廷芳
在一次闲聊中,一位朋友讲了一个既幽默又很实在的笑话。一个叫叶烨的年轻人,从985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行政单位工作,单位领导与新招录的大学毕业生召开一个座谈会。为了便于大家相互认识,单位领导按照办公室小黄拟定的仅供领导开会用的新招入人员名单,逐个点名。当领导点名“叶火华”时,没有人站起来自我介绍,领导重复了一次,还是没人应答。办公室小黄急忙示意叶烨,他才不紧不慢的说,我不叫“叶火华”,我是“叶烨”。领导脸色陡变,便借批评办公室小黄,“你怎么把叶烨写成了叶火华!”,给自己下台阶(其实小黄并没有把叶烨写成了叶火华)。办公室小黄忙应声说“领导,是我的错,把叶烨写成了叶火华。此后一段时间,办公室小黄从正科级干部提拔为副处长,叶烨则下派到一个偏远的乡镇去工作。
这虽然讲的是一个幽默笑话,但这样的事,在我们不经意中是经常发生和遇到的。那么,就这个幽默笑话中的三个人物,究竟是谁对谁错?或就每一个人的行为分析——是对还是错?其实,这是难以说清是对还是错和谁对谁错的问题。就叶烨来说,认真,不做“差不多先生”是好的;但在非本质的事情上,过于较真,不给人以台阶下,又表现得不近人情。办公室小黄灵活应变,在非原则的问题上承担了不属于自己过错的责任,给领导以面子,帮助领导下了一个尴尬的台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一些人看来,他又有拍马屁之嫌,一味顺着领导。领导因为这件事,把叶烨下放到基层工作,有挟嫌报复、滥用权力之嫌;但这又能使叶烨下基层经受锻炼,改变他从学院出来的稚气和傲气。

在这广袤无垠、地老天荒的世界,实际上也不存在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从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变化来看,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审视评判标准。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重农抑商政策占据主导地位,士、农、工、商,商居四民之末,商业行为常被视为投机取巧,不务正业。这种观念源于农业社会对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视,以及对商业逐利本质可能破坏社会秩序的担忧。在当时的价值体系下,专注于农业生产是“对”的,而商人四处奔波、追逐利益则被视为“错”的。但到近现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已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科举年代,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儒家经典的背诵和八股文的写作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然而,现代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更加多元化,曾经科举教育模式下的死记硬背经典,擅长八股文写作被重新审视,甚至被判定为存在诸多弊端,是需要改进的。
从不同角度,从辩证思维,从全面普遍的观点评判事物,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又如苏轼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核能的开发利用,为人类提供大量的高效能源电力,在缓解人类能源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满足能源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它无疑是有益的、正确的。然而,核能的使用又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福岛核泄漏等,给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生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表明科技成果也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常因观念不同而产生矛盾。父母希望子女遵循传统的职业道路,认为这样稳定且有保障,在父母的认知里是为子女好。而子女怀揣着追求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选择充满挑战的新兴职业道路。双方都有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兄弟姐妹之间常因财产分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看似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家庭内部的情感因素和实际付出难以精确衡量,谁也不能让各方都心服口服。婆媳、姑嫂、妯娌之间则常因出身不同、习俗不同、教育不同等方面的差异引发矛盾与争吵,各方都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和情感依托。“请官难断家务事”的经典之说,就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在家庭事务矛盾中,是不能简单地作对错的评判与区分的。
任何事物的对与错、优与劣,既对立统一、又相互转化切换发展的。互联网诞生之初,其积极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可谓“对”的一面尽显光芒。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深入发展,其负面效应逐渐凸显;网络诈骗日益猖獗,信息爆炸导致虚假信息低俗内容泛滥成灾,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在网络空间中面临被非法获利和滥用的风险。互联网从曾经几乎一面“正确”的创新成果,逐步暴露出诸多问题弊端。通过制定法律规定,研发先进网络安全技术,加强监督,互联网又开始朝向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又如社会人际交往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往往蕴含着对错转换的微妙逻辑。想象在熙攘的地铁车厢,人潮拥挤,一位乘客不慎踩了旁人一脚。这原本是无心之失,被踩脚者起初处于“对”的一方。然而,若此时被踩者不等对方道歉,便怒目圆睁、历声怒斥,使原本的小意外演变成一场剑拔弩张的冲突。在这电光石火间,被踩者就从占理的一方切换到了不讲文明、不讲道理的一方。
如此说来,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对与错、优与劣是复杂的、多面的、变化的、发展的。尤其在一些非本质、非立场、非原则的问题上,更难以厘清是对还是错,评判出谁对谁错。为此,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与领导、下属、同事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中,在非原则问题上就不要钻牛角尖、认死理,而应当是得理让人,给人留有余地。我年轻时,被临时借调到省直机关工作。有一次,单位要推荐一位高干子女上北京大学深造,便召开推荐评价这位高干子女的座谈会。这位高干子女在单位的工作中表现突出优秀,大家给予很高很好的正面评价。主持座谈会的领导作总结时,在赞扬之余,不经意中说:“他不像高干子女”。因为当时,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少数领导干部子女以权谋私当“倒爷”,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很不好。我当时也如同叶烨一样,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稚傲有余,还自以为很会说话,居然当着众人的面反驳领导说:“他不是不像,而是正像一个高干子女!”。正当大家面面相觑,感到错愕时,领导微笑着说:“廷芳说的对,他的工作表现、工作能力、思想水平正像一个高干子女;他平易近人,与普通干部群众和谐相处,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不以高干子女自傲,也是值得表扬的!”可见,两个说法评价都对。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借调期满,工作将近结束时,领导不是让我回到基层去工作,而是推荐我到省直机关重要部门去工作。这位领导“得理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宽宏大量,至今令我肃然起敬,在这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也一直影响着我,时时警醒着我。

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在同事间、亲友间,在茫茫的人海中,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和意见是正常的必然的。此时此刻,相对正确的一方若不能以恰当方式对待相对认识不足或错误欠妥的一方,就可能因自身态度和行为的偏差转化为错误的一方。此时此刻,相对正确的一方若能以恰当方式对待相对认识不足或错误欠妥的一方,事物就可能朝向更加和谐、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如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中的清朝康熙年间的大学生张英,不以官威压服意欲侵占张家宅基地的吴氏,而是给修书求援的家人回了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氏闻之,受到感动,也后撤三尺。这一故事教育我们要以宽容、谦让的态度处理人际关系,以和平、理智的方式解决问题,成为一个跨越时空,广为传颂,永不落幕的精神文明教材。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季羡林先生也说:“不完满才是人生”。在我们的人生中,总会遇到,耿耿于怀、斤斤计较、纠缠于对错的人和事,此时此刻,我们若是针尖对麦芒,不冷静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瞬间被愤怒冲昏头脑,死不相让,恶语相向,场面必然会陷入尴尬与紧张,双方也会糟糕烦透一整天,有的则闹到终身不来往不说话,甚至酿成后悔终生不可救药的致命事故。在人生活动的宏大画卷中,我们常常惊异的发现,许多令人懊恼不已、甚至改变人生轨迹的大事,追根溯源,竟肇始于微不足道的小事。智者常常警醒我们“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人说“容忍”是对他人行为或矛盾的被动接受,内心可能积累不满。但时间会告诉你一切真相,有些东西,要等到双方真正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唐朝的张公艺,家庭和睦,美名远扬。皇帝赞美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他一气写了一百个“忍”字。当然,宽容、忍让、容忍也是有条件、有限度、有原则的。在道德、法律、正义等核心价值领域,我们必须坚定的捍卫原则,绝不含糊。“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小事讲风格,为大事讲原则奠定基础,一个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人,很难想象在大事面前能够坚守原则。而大事讲原则又为小事讲风格提供了方向指引。倘若没有原则的束缚,所谓的风格可能会演变成毫无底线的迁就与纵容。
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我们要学会在小事与大事之间灵活切换。以风格润泽生活的点滴,让身边的人感受到温暖和善意。以原则筑牢人生的基石,坚守人生的道德、法律、正义的底线。遵此,家庭和睦安康幸福,工作顺利事业进步,社会文明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