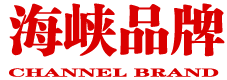四眼井
俞建峻
儿时的记忆很多,但故乡让我记忆最深的莫过于离家不远的一口井。人们称之为四眼井,传说可能是有四个泉眼得名。它坐落于闽北山城邵武的中心位置,在清伍街信义巷与其他小巷的交叉口。上世纪六十年代城里还没有自来水,街坊邻居家家都要到井边汲水。
十来岁时,我也加入去井边打水挑水的行列。井边有个固定的吊桶,用于到井里打水。井深有五六米,再加上一米多高的青石井圈,把一桶十几斤重的水提上来再倒入自家的木桶挑回家,是一件很需要体力的事。记得当时我们小孩汲水力气不够,往上提一二米都要把井绳搁在井圈上休息片刻再继续往上拎。久而久之,井圈边缘被磨得既光亮又留下一道道印痕。当我长大些后,臂力大增,提水不必半途休息,而且井绳不碰井圈,三五下就把一吊桶水拎上来,且把自家木桶装得满满当当,颇有几分成就感。可以说,这口井锻炼了一拨拨孩童,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那时民风淳朴,人多汲水时,大家都自觉排队,大人还会主动让小孩先打。有时井绳磨断,吊桶落入井下,邻近的大人都会主动用绳子拴住铁钩把吊桶捞上,重新系好新的麻绳。偶有人打水时不慎将手表掉落井下,很多邻里都会帮忙想办法用磁铁把表吸上来。一口平常的井,有许多琐碎的故事,记载着小城居民的质朴。
井水非常清澈,夏秋季节的晚上,街坊邻居的小孩经常会倚着井圈看水底的月亮,孩子们就在井边议论着天上的事,各自发挥着幼稚的想象力。在物质文化生活都匮乏的年代,四眼井给周边孩童提供了一处欢乐之源。
井水冬暖夏凉,那个年代没冰箱,夏天偶有西瓜,我们就把西瓜浸泡在刚打的井水里 “冰镇”,比现在冰箱效果还好,凉爽适度,不至于冻得磕牙。冬天,取刚打的井水洗脸刷牙,也让人觉得温暖舒适。在我的情感记忆中,四眼井是有人情温度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小孩都有很强的敌情观念。记得一天,小朋友们在一起说敌特会在井里投毒,为防止中毒,大家到河里抓了小鱼,到井边投放,说是有毒药,鱼就会翻白漂起。路过的大人看见,大声呵斥:不要往井里扔脏东西。知道我们是扔活鱼防投毒,大人们哑然失笑。直到八十年代,很多家庭自己打了水井,是用手摇汲水方式,不用提也不用挑。但水质比四眼井的水差多了,水里常有沉淀的沙土。后来家家户户都接上了自来水,四眼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不记得哪年哪月,这口井被封了,现在已岁月无痕。这口养育我们的老井,现在虽已荡然无存,但我想,它的生命力不会枯竭,它的泉流也许随着地下水汇入富屯溪,继续滋养着故乡的大地。但每次回到故乡,走到巷子口,见不到当年的水井,总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可能这就是乡愁吧。
岁月是一首歌。四眼井,承载着儿时的记忆,那种亲切感,总是进入梦乡,叩动心弦,仿佛一曲无声的旋律常在耳边回响。
实际上四眼井已成为一个地标,在家乡、在异地,至今同乡问起住在山城什么地方,只要一说住四眼井边上,大家就心知肚明了。我心中一直有个问号:四眼井究竟始于何时,最初凿井的人是谁?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吃水不忘挖井人。可惜喝水的后人真的记不住挖井的人了。但这句古训,却深入人心。我们可以记不得挖井人,但对前人的感恩之情肯定是应该有的。挖井之举虽属平凡,但正是无数口平凡的水井,惠泽了各地老百姓,不忘挖井之恩的古训,才能为大众认同,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相对于那些居功至伟的历史名人,挖井人也许是渺小的,但他们润物无声、育人不言的功绩,却价值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