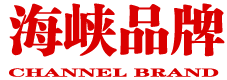最忆是溪源
许寿辉
人们常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灯如红豆最相思。那是因为有如梦如幻的乡愁,余光中的沧桑,席幕容的清新,李白“明月”式的感怀,最是平常心当是贺知章的“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那逝去的童年,那遥远的故乡,那袅袅升起的饮烟,魂牵梦绕着的总是一种沁人心脾的醇香,一种让人品味无穷的心醉。

鬓霜还桑梓,从都市熙攘到山乡野趣,剪得一段清幽时光,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溪源。“溪源好,晨雾漫山岚;古井,青砖,樟木茂盛,山风野味酒浓酣;游客乐悠然”,在高荣娇老师笔下,溪源,已然是建阳美丽乡村之翘楚。其实,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溪源的灵魂密码恰恰是深藏在老街深巷之中的往事、趣事与故事。

走进老街,扑面而来的是一条石阶铺成的悠悠官道。石板,早已被大小各异的脚步磨得发亮、凹凸,但曲径通幽,可直达考亭书院。两侧的房屋灰瓦泥墙,屋檐下悬挂的灯笼,古朴庄重,依旧惊艳;巷口的下马石,侯官亭,与弄里的塾庠序学,比屋弦歌,耕读传家的印迹相辉交映,充满了传说。一个转角,一口古井,一座老宅,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无不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诠释自己的名字与辉煌,最值得诉说的当是溪源这个美丽名字的由来,是顾名思义水之源吗?非也!答案在哪?我等寻寻觅觅,往来穿梭于街头巷尾一一

有人曰:是村中央修建于嘉靖年间的“吕氏宗祠”。堂前高悬的御赐“文魁”牌匾最是醒目。相传,始祖吕湮,为唐朝宰相,一生为民,清廉刚正,因治乱有功得朝廷御赐门戟,以文官武赐而扬名天下,后因遭奸臣诽谤而携家眷逃遁至此,吕湮为何选择在此落脚及其当时建村的规模,族谱鲜有记载,比较详细是淳熙乙末(公元1175年),与朱熹、张栻齐名的“婺学”领袖吕祖谦由浙江金华来到建阳寒泉精舍,拜访朱子,彼此把酒抒怀,谈儒论道,为了让理学大厦前的初学者有一把拾阶而上的梯子,两人决定合编《近思录》,为寻找灵感,常到周边山水游历沐浴,伐木筑梯,可以说,是这里的涓涓流水,似源头“活水”,有如溪源其名,为理学名篇《近思录》的最终完成注入了鲜活的生机。吕祖谦亦深深地为这片地理开阔、秀美而灵动的山川而折服,赞曰:“游丝浩荡醉春光,倚赖微风故故长;几度莺声留欲住,又随飞絮过东墙”,认定是一块可以“卜居”的风水宝地,还把女儿嫁给朱熹三子朱在,遵其遗训,吕氏后裔亦陆续迁徒到此,沿溪栖息,这是溪源名称的由来之一。至明万历年间,最终形成了以吕氏为主的上、中、下溪源三块群居地,繁衍生息了近千年。“正本清源臻大治,慎终追远达长安”,祠堂由吕祖谦第15代孙吕佛定在虎井山上始建,堂墙四周悬挂着的是吕祖谦的《家范》及其“曰清、曰慎、曰勤”的三字官箴等,一个家族的精神从此飘跃群山,洞穿历史,滋养、激励着一代代的溪源人,“玉堂金马登高第,故甲前贤励后昆”,与祠堂隔路相望的是为纪念明万历年间科举高中的乡贤吕武良而立的“探花亭”,还有上溪源的武状元等等……

又有曰:是村尾的那棵“三生树”,又称“许愿树”。它,历经700多年的风雨,有一种饱满钝挫的含蓄,一派洗尽铅华的风骨。相传,也是吕氏后人为纪念朱熹与吕祖谦的功德、友情,专程从考亭那棵传神的“千年根抱佛”大樟树嫁接、移栽而成的。在这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阳光映照下的枝叶闪烁着翡翠般的光泽,时而在风中摇曳,如同一个绿色的精灵,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时而又微微歪着头,亦仿佛在默默诉说着张生与吕淑兰那凄美的爱情故事,如画如梦,一个值得青年男女去谈一场恋爱的绝好去处,邂逅的美丽。

再有曰:是虎井山上的“陨石坑”(俗称“星星坑”)。蕴藏着一个远古时期神仙降伏牛头怪的神话传说……年与时驰,从水之灾到水之源的演绎,“陨石坑”在当地百姓心目中,俨然就是那口神奇的“半亩方塘”,而今,波光潋滟的塘中央赫然伫立着的是山寨版的“天光云影亭” ,“为有源头活水来”,村民们还专门修建了朱子纪念墙,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雕刻其上,并在村口的溪边修建了“问渠亭”,悬挂着“漫赏方塘开鉴影,且循活水探溪源”的楹联,这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愿景,愿此诠释溪源这个美丽名字的由来。
无寻处,惟有少年心,悲喜搁心头。

正午时分,我等且行且思,随风起,抬头眺望,土褐色的泥墙,渡着一片片冬日的暖阳,一丛丛、一簇簇或淡红,或浅黄的光影在匆匆忙忙行走,斑驳的纹理肆意纵横,书写的分明是岁月的轮廓与沧桑;小巷深处,回首相望,多少发小、兄弟,都已渐行渐远,过去人声鼎沸的几个大户人家,也是一片岑寂荒凉,唯有梁上的呢喃,似曾相识,不老的燕子不惊不怕,低头与我们对视,又高傲地抬起头来,巷尾的断壁残垣下是几个形影相吊的老人佝偻着背影,几只黄狗“汪汪〞的叫声,如最后的守望者。


溪之源,水之韵,目之所及都是记忆,心之向往皆为过往,一幕幕熟悉的场景,承载了太多的情愫,朴实无华,透着丝丝悲凉,又温润人心一一
遥想当年,这里的暮染烟岚,那是何等的氤氲馨香!最是难忘的是吕家巷口的那一泓道光年间而掘的老井 ,井边四周,仿佛就是村民的信息交流中心,荡漾着的是那融洽热闹的气氛,东拉西扯,荤荤素素,口嘴没遮没拦,简直就是一幅上天入地,滋养生命,灌溉五谷,也浇灌出一种乡土文化的图景!

此刻,我静静地站在被苔藓轻轻覆盖的老井边,聆听它的耳语,感悟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摇曳的记忆,如歌如赋,小时候常听母亲讲 ,祖上一辈在村里亦是名门一族, 外曾祖父曾是县里的参事,而且辈分很高,我亦感同身受,外公的家是一幢明清结构的四进式祖房,后山果园七八棵挂满枝头的,是桔树与梨树,在物质贫乏的年代,算是一个殷实之家,乐善好施的外公,还兼乡里农信社的代办员,家的大堂常是高朋满座,无论大小见到外公都是尊称“叔公”,缘此,从小我便享有“外甥王”的待遇,那一句句“辉仔,辉仔 ……”人见人爱的亲切,声声在耳!都说人生如梦,而“梦”中的景致色彩,往往取决于对你影响最深的人,这个人就是我的舅舅,他当年是建阳农校毕业的中专生,后来成了回乡知青,我常跟随着他,成了福州“老三届”知青们哪儿游走混迹的“跟屁虫”,每天听他们海吹胡侃,懵懵懂懂,耳濡目染,烙印最深的,除了舅舅拉得还算悦耳的二胡,便是寄住在外公家的一黄姓知青,戴着一副眼境,斯斯文文,还在村小学兼代课老师,有文化,特别会讲故事,每当夜幕降临,他总会准时来到巷口与井边阡陌交织的供销社小卖部,给一群的孩子们绘声绘色地讲起故事,关键时又常常是卖关子,吆喝一声:欲知后事如何?打一壶井水来!咕噜咕噜喝下,清清嗓子再叙,“滥竽充数”“画蛇添足”“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等,这些很多年后方知都是出自《吕氏春秋·察今》的寓言故事,我在上小学时已了然于胸,主要得益于他的“演讲”,吕家巷口的老井边尘封着我孩提时的求知、憧憬和欢乐,可谓是我文史兴趣与爱好的启蒙之地,怪不得高考时,我的数学只有可怜的8分,人生漫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切尽在冥冥之中,原来这才是我珍藏在内心深处最美的乡愁! 时光煮雨,岁月流金,而今,这个快乐的圣地,伴随着时代的风雨被卷走了、吹散了、湮灭了,但溪源有福,因为,“活着”的老井有知,那是山乡巨变,让自己可以“坐井观天”,而“含笑井泉”了,还“井”上添花,成就了另一番风景——乡村旅游最火红的“打卡点”,如织的游人在俯首清冽的井水,在仰望蓝湛的天空,在抚摸硬邦邦的井沿,在一个个“咔嚓”声中留下了怀旧,寄寓着那份岁月和生命的韵味。

人生无处不相逢,老井边竟与发小“老道”相遇,长大后他在检察院,我在法院,再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省城,退休后两个同道“闺土”相见,模样没变,变得的是头上曾经的斜流海都变成了“地中海”,感叹岁月无情,感怀童真可贵,童趣难忘,记得他长我2岁,父亲是村卫生所的医生,人以类聚,从小就是我仰视的“头儿”,那时候的电影多以英雄人物为题材,像《铁道游击队》《沙家浜》等等,玩的游戏也模仿电影情节,在后山的松树林,我们一起“守阵地”“攻山头”“侦察夜袭”,并肩“战斗”,他既是“指挥官”,又是冲锋陷阵的能者,一次他戴着一个竹编的“头盔”迎敌,被飞来的石子砸出了血,仍轻伤不下火线,每次都把“敌人”打的落荒而逃,还有那一起下田捉泥鳅、溪中抓鱼虾……一点点、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

身处他乡,故乡,永远是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家在梦中何时到,春来江上几人还”,很多时候,故乡都是我在夜里无意仰望星空的脸庞,看见流星坠落,坠落在故乡的方向,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史铁生在《消失的钟声》中写道:人的故乡,并不止于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对此,我深以为然,追往事,童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醉在流霞!
“阅尽千帆,归来仍少年”,站在这梦想起航的地方,一阵徐来的清风,轻柔地抚摸着我的脸颊,不知是我在念故乡,还是故乡在念我.....
风起,我心飞翔!